聚焦全科医生难培养:发展空间小 待遇留不住人
1
从关注“病”转向关注“人”——
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全科医生培训应更注重医患沟通、团队合作、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卫生服务等内容
杨瑞红做全科医生有些年头了。原来她是一名内科大夫,四五年前,她所在的山东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荐她参加了全科医生的在职培训,那是淄博市较早一批全科方向的转岗培训。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年多,也在培训基地各科转了一圈,考上了全科医生的执业资格证。”但是,工作几年后杨瑞红发现,自己还是最擅长内科,其他科都不太擅长,她特别希望能再脱产深入地学习,拓展相关各科的知识。
杨瑞红的困惑似乎延续到该中心正在接受全科培训的杜新菊身上。杜新菊在区医院已经轮转了十几个科室,可是不太自信,她认为很多工作中需要用到的知识没学到,比如怎么和居民沟通、怎么进行健康教育等。
对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潘志刚认为,我国各地社区卫生服务内容和方式都不统一,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培训中,授课的老师大多是二级以上医院的专科医生,缺乏全科方面的知识培训,时间也比较短。这与我国的医学教育模式、医疗结构有关,目前我国以专科教育模式为主,医疗资源向三级医院集中。本应处于金字塔底座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一直未能建立科学规范的培训体系和制度,导致低水平重复培训多,政府投入的效果不太明显。
《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可见,全科医生是预防疾病的一道防线,其工作重心已从过去的“治”转向“防”,这是医学模式的变革。全科医学的培训模式必须随之转变,从关注“病”转向关注“人”,更加注重医患沟通、团队合作、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卫生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培训。
台湾联新国际集团总执行长张焕祯认为,这正是全科医生区别于专科医生的最大不同,即以“全人”的角度去理解病患的健康需求,而不仅仅是治疗疾病。以失眠为例,如果去看神经科,医生只会问患者是否脑部等器官上出了毛病。但如果是碰上训练有素的全科医生,除了器官之外,他还会关注病人是否因为情绪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引起了失眠。
2
从求数量转向重质量——
要建立人才准入、评价与退出机制,明确职业发展前途,让全科医师能真正留下来、用起来
北京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平,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出了一套全科的规范化教研方法,迅速提升了中心医生的服务能力,该中心也成为全国全科医师的培训基地,杜雪平因此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笹川卫生奖”。
事实证明,全科医师培训不能急于求数量,必须要进行规范化培养,建立人才的准入、评价与退出机制,明确职业发展前途,让人才能真正留下来、用起来。
上海从2000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试点工作。去年,上海市将全科医师培训全面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今年5月,“上海市中美全科医学培训与交流中心”成立,推出“5+3”全科医师培养新模式,即以5年医学本科学历教育为基础,再加上3年的全科医师培训,进一步建立标准化的全科医学培训体系。
从2006至2009年,上海共招录全科医师培训生367人,目前已全部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员成为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骨干,担起了“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在台湾,全科医生的培训过程十分严格,必须要接受7年医学院培训、1年全科培训和3年专科培训。1988年,台湾正式将全科医学作为重要学科来发展,每年有150至180名全科住院医生训练名额,约占全台湾医学院毕业生的14%,在所有科别中居第四位。” 张焕祯介绍说,全科医生培训时,收入是毕业后的一半。因为培训合格的医生就业后的收入很高,所以大家对培训时付出的艰辛都较认可。
比照台湾的情况,张焕祯认为,中国内地全科医生的培训应该选择“两条腿”走路。一是依靠全科医生制度,对全科医学人才进行规范化培训,需时3年;二是可以从县医院抽调骨干医生进行全科医生培训,为时1年。鉴于全科医生培养周期较长,在正规培养的全科医生还没有下到基层前,抽调县级医院的医生进行全科医生培训,让他们先负起全科医生的职责。
人才培养出来后需要有评价机制。职称是衡量医生业务能力的一把尺子。据潘志刚介绍,目前在对全科医生进行职称评定时,基本参照其他专科的体系,只是把标准和要求适当降低。原因在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不太清楚全科医生岗位的职责。因此,要建立全科医生的评价机制,建立职称系列,首先应该把社区功能服务包定义清楚,然后根据岗位制定相应的职称系列及考核方案。
3
从单项激励到综合配套——
实现对全科医生有效激励,需要一个好的机制,同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事、分配、补偿、管理等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杨瑞红每周要入户两次,给慢性病患者、65岁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做随访,平时还要出诊,工作量较大,内容较庞杂。但是很多项目收不上钱,杨瑞红觉得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体现不了全科医学的价值。她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董砚奉说,全科医生只比其他医生的收入多15%左右。
四川新津县花源镇公立卫生院院长杨成认为,既然接受了全科培训,医生的能力会相对高点,应在待遇等各方面有一些倾斜,否则基层还是留不住人。
《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指出,由于社会认同度低,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吸引和稳定人才,条件较为艰苦的山区、民族地区和贫困边远地区尤为突出。2003—200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流失的正高、副高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分别占在岗相应职称人员总数的35.7%、10.1%、9.5%。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益新说,实现对全科医生的有效激励,需要一个好的机制,必须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事、分配、补偿、管理等制度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2005年以来,上海以强化公益性为核心,启动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推动运行机制转换。通过补偿机制、收入分配机制、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与服务数量、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挂钩的分配制度。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还对社区的全科医生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规范化培养后的学员被基层社区卫生服机构录取后,与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交纳社会保险。外省市户籍学员可申请办理上海市引进人才居住证。
这些改革,让来自安徽的刘忠仁大夫感到安心。2010年,经过3年的规范化培养,他正式成为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每月收入达到五六千元。
“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年多,最大的感受是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刘忠仁坦言,他的全科医学专业知识比较扎实,因此很快得到了居民的信任。“我能感受到这几年全科医生地位的变化。当然,如果能够在经济收入上予以适当提高,就更好了。这一行,还是有干头的。”他说。
按照国外的经验,全科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签约服务收费,我国也将参照该办法。潘志刚认为,国外经验表明,服务内容越多,每名全科医生照顾的居民数越少。鉴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三级医疗分工协作局面,去哪个医院看病,主动权掌握在患者手里。因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推行首诊制,才能真正实现签约服务。
据了解,我国正考虑先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强制性首诊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通过医保支付实现全科医生首诊,直接到大医院就诊者提高自付比例。 (李红梅 王有佳)
上一条:农民工大拇指被压伤后染上重症破伤风 全身僵硬
下一条:建筑工作业时出意外 金属钻头插入颅内达10厘米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网络
木门 装修 橱柜 油漆 壁纸 木地板
吊顶 十环 大理石 涂料 灯具 厨房
水泥 板式家具 儿童房 监理 衣柜 设计师
卧室 板材 洗衣机 石膏板 陶瓷 实木家具
铝合金 玻璃 田园 钢材 窗帘 书房
松木 化学建材 冰箱 热水器 洁具 地板砖
办公室 客厅 门窗 中式家具 金属家具 空调
儿童家具 墙纸 门 餐厅 儿童 店面装修
衣橱 导购 装修设计 背景墙 家居时尚 店面
第三批2008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发布


中国环境标志 十环产品标志
十环产品标志: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和国家建筑材料展贸中心发起,由企业自律,十环产品评定办公室和消费者监督,企业从设计到生产以及销售都要履行绿色环保公约,建材和装饰材料可以申请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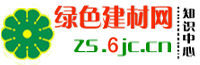
 分享:
分享:













